李永红丨互斥型对向犯的控辩裁判与逻辑谬误
10天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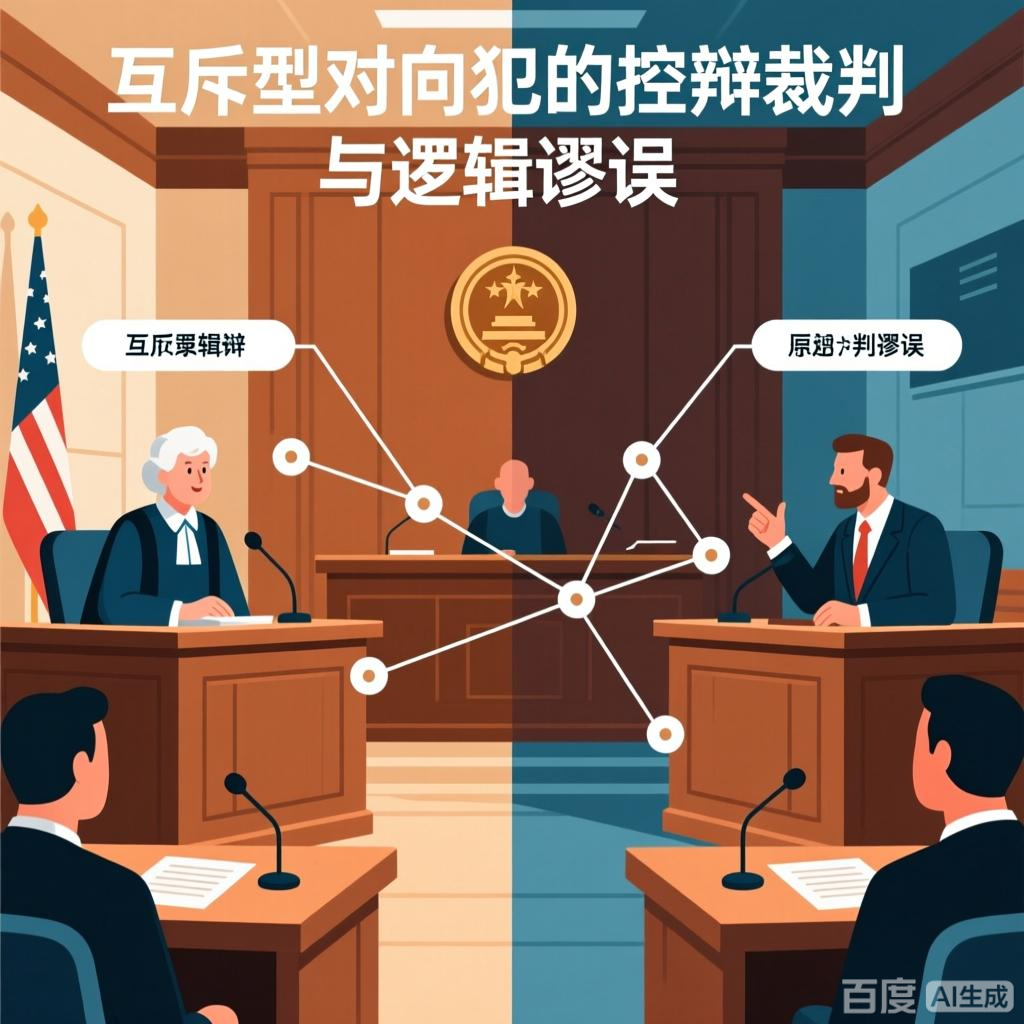
来源:司法方法公众号
一、起诉指控、无罪辩护和法院判决
骗取贷款(票据承兑和金融票证,下同)罪是指以欺骗手段致银行形成错误认识而取得银行贷款、金融票证并给银行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如果贷款不是通过欺骗手段而是基于银行的故意违法发放而取得,则不能认定为骗取贷款罪,更不能认定为对向犯违法发放贷款罪、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的共犯。
1.起诉指控
某市人民检察院的起诉指控:HF银行该市支行负责发放贷款的负责人与某企业集团实控人建立金融配套服务关系实施银企合作,支行为了完成上级分行下达的存贷款考核任务、扩大存款规模、增加贷款指标而主动发放贷款、出具金融票证,企业集团取得贷款后再回存该支行,支行承诺承担贷款发放、金融票证出具与回存过程中的利差损耗、费用开支并使企业有一定的获利。检察院认为银企双方分别犯有违法发放贷款罪、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和骗取贷款、金融票证罪,要求法院追究双方的刑事责任。
2.无罪辩护
辩护人无罪辩护的主要观点:刑法第175条之一规定的骗取贷款罪和刑法第186条规定的违法发放贷款罪、第188条规定的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是具有互斥关系的对向行为。在银行人员违法发放贷款罪、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成立的情况下,取得贷款和金融票证并回存银行的企业人员的行为,既不构成骗取贷款罪,也不构成银行人员违法发放贷款罪、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的共同犯罪。
3.一审判决
法院审理后,未采纳无罪辩护意见,以违法发放贷款罪、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对银行人员定罪判刑,以骗取贷款罪对企业人员定罪判刑。
二、案件证据和行为事实
控辩审各方对在卷证据及其证明的事实并无根本分歧。
1.关于银企合作存贷款业务的行为动因
在卷证据证实,HF银行某市支行根据上级分行领导的要求,为完成存贷款任务、扩大存款规模、增加贷款指标而主动发起与SX企业集团建立金融配套服务关系开展银企存贷款业务合作。起诉书亦如实认定:“被告人陆某某三人运用担任HF银行某市支行相关岗位的职务和上级银行指派下挂的职权,为了完成HF银行上级分行下达的存贷款任务指标,特别是2015年3月以后,分行行长曲某(另案处理)明确要求以存贷业务合作的方式完成存贷款任务指标,被告人陆某某三人先后与被告人何某某等人合作,由被告人何某某等人用实际控制的SX企业集团公司配合开展银行各项存贷款业务。”该事实表明,银企双方所实施的行为,肇始于HF银行该市支行根据上级银行要求而主动发起的银企存贷款业务合作,贷款发放和金融票证出具并非源自企业的骗取,而是基于银行为了自身利益而故意实施的违法发放和违规出具。
2.关于银企合作存贷款业务的行为模式
涉案贷款、金融票证业务的办理,均是在银行工作人员授意、帮助、指点之下所为,银行对贷款资料、资金用途等均有明确认知,银行并未受骗、当然亦未产生错误认识。不仅数十份言词证据一致证实双方在业务合作中企业没有欺骗、银行没有受骗,而且在案书证《银行某市分行SX企业集团调研组会议纪要(2016年8月22日)》明确记载“继续开展金融配套服务:2016年3月份已与SX企业集团就战略合作达成初步方案:1.SX积极配合分行CIB存款工作做好金融配套服务;2.SX在存款续做过程中减少的资金流要予以及时回补,通过2 - 3年时间,逐步建立良性、规范的合作”。书证内容印证了言词证据的内容,足以证明以下事实:银企双方的存贷款业务合作主要方式是先由银行发放贷款再由企业回存银行,因存贷利率不同而必然发生利差损耗,也会产生运行费用,银行承诺承担这些损耗和费用并让企业有一定的获利。这种模式中的贷款显然不可能具有真实的交易背景,银行所起的作用不仅仅是明知交易背景不真实而放任,而是故意以这种不真实的交易背景发放贷款、出具票证,目的是增加贷款指标以完成考核任务。该事实表明,涉案贷款发放和票证出具,由银行故意违法违规实施,根本不存在企业骗取银行贷款或金融票证的事实。
3.关于银企合作存贷款业务的行为结果
涉案贷款、金融票证中的资金绝大部分以企业存款的形式重新回流HF银行,HF银行支行实现了完成扩大存款规模、增加贷款指标以完成考核任务的预期目标,而SX企业集团却并未获得银行承诺支付的损耗、费用和一定的利润。当然,也有部分贷款尚未偿还。无论言词证据还是书证,都证实了涉案贷款资金回存银行的事实。在这种业务合作中,银行虽承诺支付企业损耗、费用和利润,但最终未依约支付而使企业遭受损失,而银行人员因贷款指标增加却获得了巨额利益,其部分贷款因各种原因未能归还尚可通过诉讼追偿,即使有损失,也是银行主动违法发放贷款所致,而不是企业骗取贷款的结果。
综合以上事实,本案银企双方存贷款业务合作的动因是银行通过做大存款业务量而增加贷款指标,模式是银行主动向合作企业发放不以真实贸易为背景的贷款或者出具金融票证、企业获得资金后再将资金回存银行,效果是银行通过银企合作故意违法发放贷款、违规出具金融票证谋取了利益,企业按照银行安排所作的配合不但未获利反而遭受了损失。指控企业骗取贷款显然与证据证明的事实不符。
三、法律规范、裁判规则和刑法学说
违法发放贷款、违规出具金融票证和骗取贷款、骗取金融票证属于对向行为,但罪名、要件和法定刑不同。根据刑法规定和刑法学说,两罪存在互斥关系而不能同时成立,在银行故意违法发放贷款、故意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的情况下,企业人员既不构成骗取贷款金融票证罪,也不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的共犯,否则,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1.对向犯刑法规范
对向犯是指双方互为行为而成立的犯罪,对向犯在刑法上有多种不同的处理方式,因而学理上也有各种分类,如必要共犯的对向犯和片面共犯的对向犯,互斥型对向犯和相容型对向犯等。狭义的对向犯仅指双方行为都成立犯罪的情形(包括同一罪名和不同罪名),广义的对向犯还包括行为具有对向关系但一方行为构成犯罪而另外一方行为不构成犯罪的情形。我国刑法规定了四类对向行为评价模式。
第一,构成共同犯罪的对向犯:对向行为按同一罪名定性,当然能同时成立犯罪。比如重婚罪、非法买卖爆炸物品罪、非法买卖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和聚众斗殴罪等,双方的对向行为在罪名、要件和法定刑上完全相同。这种对向犯属于相互兼容、可以同时成立犯罪的共同犯罪行为。
第二,具有相容关系但分别构成不同犯罪的对向犯:对向行为按不同的罪名处理,可以同时成立不同罪名的犯罪。比如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支付财物的一方构成行贿罪,收受财物的一方构成受贿罪,双方罪名、要件和法定刑不同。对这种对向行为不能按共同犯罪处理,既不能在行贿罪成立的情况下将支付财物的行贿方按照收受财物一方的受贿共犯处理,更不能在支付财物一方不构成行贿罪时按照受贿罪共犯处理。
第三,具有互斥关系不能同时成立犯罪的对向行为:对向行为既不能同时成立犯罪,又不能成立共同犯罪。如骗取贷款、金融票证罪和违法发放贷款罪、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因两罪均是故意犯罪,若取得贷款的一方实施骗取行为,发放贷款的一方形成了错误认识而发放贷款、出具票证,那么因为被骗而发放贷款、出具票证的一方便缺乏犯罪故意;若银行故意违法发放贷款、违规出具票证,则取得贷款和金融票证的行为便不可能是欺骗导致银行形成错误认识而发放、出具,即使取得贷款和金融票证的一方配合银行弄虚作假,其弄虚作假行为也因银行的故意违法发放、故意违规出具行为的介入而与贷款发放、票证出具之间因果关系被阻断。
第四,一方有罪而另一方无罪的对向行为:刑法只追究对向行为一方的刑事责任。这种情形在刑法中多有规定。如,刑法第389条规定的行贿罪,不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贿行为不构成犯罪,受贿方无论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正当都构成受贿罪。又如,刑法第228条规定的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出让方有罪,受让方无罪。再如,刑法第410条规定的非法批准征收、征用、占用土地罪和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罪,批准方和出让方有罪,报批方和受让方无罪。
2.互斥型对向犯裁判规则
违法发放贷款、违规出具金融票证和骗取贷款、骗取金融票证属于具有互斥关系的对向行为,双方行为因法律对要件的规定而不可能同时构成犯罪。对银企双方来说,若贷款系银行故意违法发放、金融票证由银行故意违规出具,则企业取得贷款、金融票证的根据就是银行的故意违法发放和违规出具,而不是企业自己的骗取。
对企业来说,即使取得贷款和金融票证时有作假行为,也因银行明知甚至授意而故意违法发放、故意违规出具这一因素的介入,使作假与取得之间的因果关系中断,取得方的行为不可能构成骗取贷款和金融票证罪;同理,对银行而言,若贷款发放、票证出具是因为银行被企业欺骗而形成错误认识,那银行就不存在违法发放、违规出具的犯罪故意,没有犯罪故意当然就不成立违法发放贷款罪和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
本案证据已经证明,贷款发放和票证出具是银行为了完成任务指标而故意主动违法违规所为,企业的行为是根据银行的指令进行的,很明显贷款发放、票证出具不是企业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导致银行产生错误认识所致。经检索既往案例,在司法实践中对对向行为的裁判,既有正确适用法律的先例[如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2014)湖浔刑初字第410号刑事判决书,以银行出于经营上的考虑而不是因被告人提交虚假资料而陷入错误认识继而发放贷款为由,判决骗取贷款罪不成立],也有同时认定违法发放贷款罪和骗取贷款罪的错误裁判先例,但将取得贷款一方认定为违法发放贷款罪共犯的做法则极罕见。
迄今为止,法院从来没有把行贿人按受贿共犯处理的先例,原因正在立法者在制定刑法时通过规定不同的罪名、要件和法定刑而将双方行为区别对待了。如果可以按共犯处理,那么所有的对向犯都像重婚那样处理就行了,又何必费神费力地在制定刑法时对众多对向行为分别规定罪名、罪状和法定刑呢?
3.刑法原则与学理解释
对不构成骗取贷款罪的获取贷款和金融票证的行为,若按违法发放贷款罪、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的共犯处理,则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因为,既然刑法已经对不同对向行为分别作了四类不同的处理,那么,司法裁判就应该依法评价而不应混淆法律的不同规定。在骗取贷款罪法定刑轻于违法发放贷款罪、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的情况下,将不构成骗取贷款轻罪的行为按违法发放贷款罪、违规出具金融票证重罪追究刑事责任,必然导致构成骗取贷款罪的行为处理更轻而不构成骗取贷款罪的行为反而处理更重的荒唐结果,显然违反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关于对向犯,刑法学者指出:“第一,既然刑法仅将骗取贷款的行为规定为犯罪,那么,如果对没有采取欺骗手段的违法申请、接受贷款的行为以违法发放贷款罪的共犯论处就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之嫌。”“第二,将不构成骗取贷款罪的行为以违法发放贷款罪的共犯论处,也违反罪刑相适应原则。”张明楷教授在对比《刑法》第186条和《刑法》第175条之一规定的法定刑以后指出,因两罪法定刑轻重不同,骗取贷款罪轻,违法发放贷款罪重,若将取得贷款一方作为违法发放贷款共犯处理,就必然造成取得贷款的一方不构成轻罪却能按照重罪共犯认定反而处罚更重这一明显不合理的情况(参见张明楷:《对向犯中必要参与行为的处罚范围》,载《比较法研究》2019年第5期)。坊间有一个传说:张教授认为无罪的那是真无罪,正如陈教授认为有罪的那是真有罪一样。
四、逻辑谬误、控审误判和刑事辩护
公诉机关起诉书和法院判决书对同一笔贷款在认定银行故意违法发放的同时又认定企业人员骗取,这种指控和判决在推理论证上存在明显的逻辑谬误。逻辑谬误分形式谬误和非形式谬误。形式谬误(Formal Fallacy)指在逻辑推理过程中论证形式即逻辑结构无效而导致的错误,如肯定后件或否定前件等谬误;非形式谬误(Informal Fallacy)指论证中由于前提、结论的内容或相干性在语境或语义上存在问题导致的错误,如言词定义谬误和诉诸人身谬误、转移或偷换论题谬误、稻草人谬误、相干性谬误等实质谬误。
演绎推理常见的思维方式有:三段论,假言推理(“如果……那么……”,有肯定前件式和否定后件式两种有效形式,相应的存在否定前件谬误和肯定后件谬误两种形式谬误),选言推理(“要么……要么……”,有否定肯定式和肯定否定式两种有效形式,也存在对应的逻辑谬误)等。在选言推理中,把“不相容”析取误当作“相容”析取的谬误通常被称为忽视不相容析取谬误。该逻辑谬误的核心是错误地认为两个互斥的不相容选项(如故意违法发放贷款和骗取贷款)同时为真,从而忽视了二者之间固有的矛盾关系,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举三个例子。
第一个是“开关状态”:真实情况(不相容)是“这个开关要么是开着的,要么是关着的”,谬误推理(相容)是“这个开关同时既是开着的又是关着的”(就如同“一笔贷款既是故意违法发放的又是非故意违法发放即被骗取的)。这显然违反了排中律,一个标准的开关只能处于一种状态,两者互斥,认为它们可以共存就犯了假析取谬误。
第二个是“地理位置”:真实情况(不相容)是“你现在要么在中国境内,要么在中国境外”,谬误推理是“你在中国境内,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你不在中国境外”。这显然很荒谬,“境内”和“境外”的定义本身就是互斥的,认为一个人可以同时处于两地,忽视了“境内/境外”这个不相容析取选项的本质。
第三个是“法律判决”:真实情况(不相容)是“法庭判决被告人要么有罪,要么无罪”,谬误推理(相容)是“既然有罪或无罪都有可能,那意味着一个人同时既有罪又无罪”,后者显然不可理喻,面对同一个指控,有罪和无罪是相互否定的状态,非此即彼,不能共存,既有罪又无罪表明法律逻辑彻底混乱(正如对同一笔贷款,既由银行故意违法发放又因被企业欺骗而非故意或过失发放)。
肯定析取谬误的本质是误将相容关系当作不相容关系,推理过程是错误地以肯定一个选项来否定另一个,例如“他是医生,所以他不是志愿者”(错误,因为二者完全可能兼具);假析取谬误本质是误将不相容的两个选项当作相容选项,推理过程是错误地认为两个互斥的选项可能同时为真,例如“开关要么开要么关,所以可能既开又关” (错误,因为开和关两个状态完全互斥不可兼具)。
如前所述,我认为影响司法公正的因素有四:司法制度(法理)因素,职业道德(伦理)因素,认知偏差(心理)因素,逻辑谬误(真理)因素。不讲理不公正的司法诉讼,究其原因,除了制度法理和道德伦理因素,就是认知心理和逻辑真理因素。无论司法官员还是在野法曹,都应该有自知之明,既要有规定性判断力,又要有反思性判断力。只有“知无知”,才会通过学习变得有知;只有换位思考,才能处事公道。知识即美德。很多让人匪夷所思的做法,即使出自认知偏差和逻辑谬误,也与伦理有关,因为让自己不要停留于无知也是一种道德责任。下午在高铁上跟一位青年才俊微信聊起这个话题,他说据他的观察,有些错误是人为预设了一个错误的结果,明知推论存在逻辑谬误而故意为之。呜呼哀哉。
相关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