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红丨知识的诅咒、框架效应与法律人的沟通策略
5天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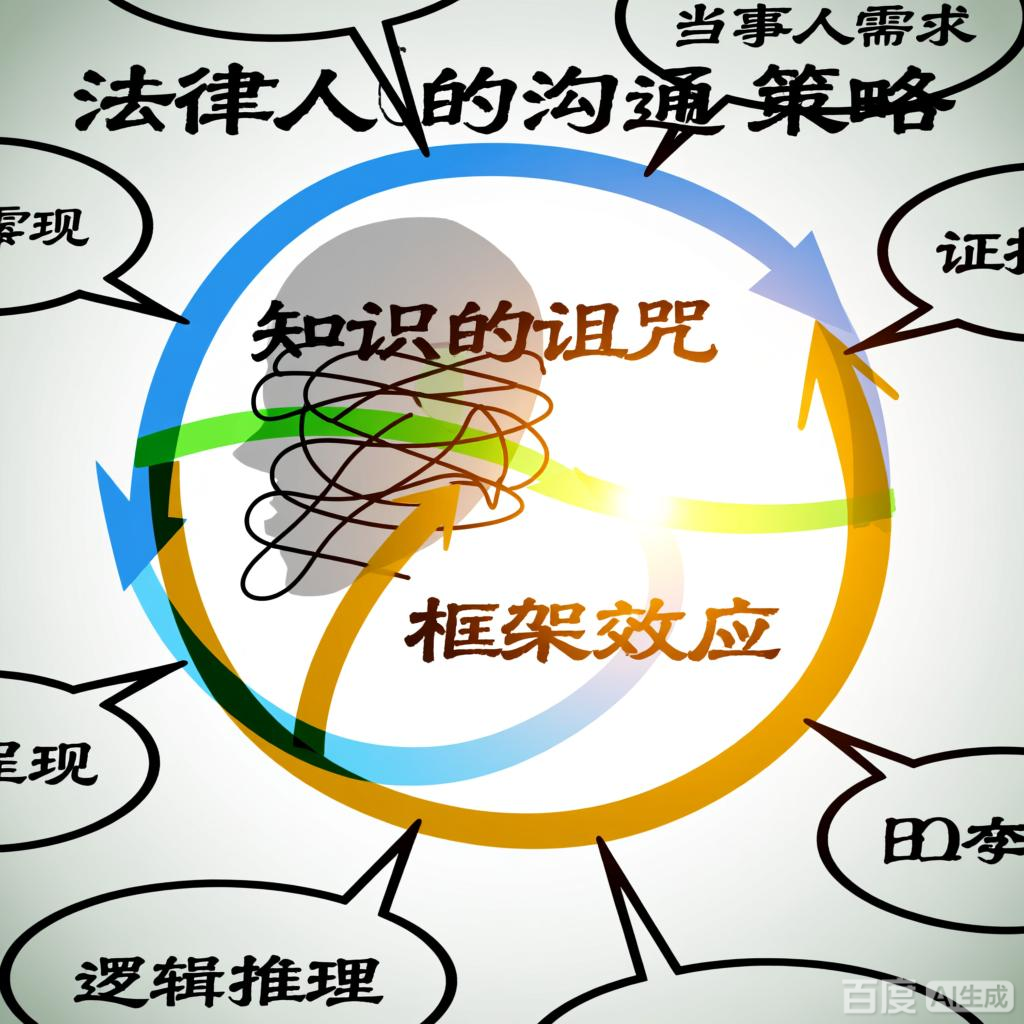
来源:司法方法公众号
认知偏差与逻辑谬误系列之五知识的诅咒、框架效应与法律人的沟通策略
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业界公认某某人很有学问,文章写得很好,但是口才却一般,不善于沟通交流。正如专业水准还算不错的律师接不来案子,而一些水平有限却善于迎合客户心理的巧舌如簧者总是不愁没有案源一样。 其实,法学界也存在这样的人,比如被称为英国法理学之父的奥斯丁,就是一个学术很牛但讲课却极为沉闷乏味因而不受学生欢迎的人。有人说这种现象可能与学科有关系,比如法理学课程,对于大一的新生而言,是新专业的第一门专业课,学生毫无概念,近乎小白,而课程内容又抽象晦涩,要让初学者理解,的确不容易。但是,大学里面也有不少法理学老师被评为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说明这种归因并不靠谱。其实,这是一种名叫“知识的诅咒”(The Curse of Knowledge)的认知偏差现象。这种现象几乎每个人都会遇到,它似乎植根于人类的认知活动中。我记得在上小学的时候,就是没法理解算术应用题的答题方法,每次回答都会把提问抄一遍再接着写答案,这种多此一举的写法把老师气的不行,可我不知道咋回事儿当时就是弄不明白正确的答题方法。很多家长在辅导自己孩子写作业时常常会很崩溃:“明明极为简单的东西,这孩子咋就弄不懂呢?”其实不怪孩子,而是老师或家长陷入了“知识的诅咒”,忘记了自己是经过多少年训练都大学毕业了才觉得作业“很简单”的。所谓知识的诅咒,是指当一个人掌握了某种知识后,难以想象无知者的状态,从而在沟通中假设对方具备相同的背景知识,最终导致沟通障碍甚至令人误解。一旦我们知道了某件事,我们就想当然地认为别人也知道,并以此为前提与别人沟通,自己讲得头头是道,别人听得云里雾里。这相当于我们的思维被现有的知识“污染”了,导致我们无法准确理解和评估他人的无知状态。知识渊博的人未必是有效的沟通者和优秀的老师,因为沟通和教学需要深刻理解他人的状态,并且能将复杂知识“翻译”成他人可理解的简单语言。
前几天,我那位持有注册会计师资格的妹妹问了我一个跟律师有关的问题,说有一家律所在他们公司开发的某个平台上为律所和律师打广告,他们公司开了广告费发票,律所说律师不能打广告因而不能开广告费发票,要求开技术服务费发票。她说,开广告费发票的业务要交文化事业建设费,不让开广告费发票,文化事业建设费就不能交,而事实上又是广告业务,公司觉得这样有法律风险,所以就来问我。我告诉她,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可以打广告,正如医院可以打广告一样,虽然浙一浙二这样的大医院几乎不打广告,但是你不能说那些肛肠医院、不孕不育医院的广告就是违法的。然后我就把全国律协的有关规范发给了她,用于证明律所和律师是可以打广告的。然后她就问我第四条不是明明规定“公司律师、公职律师和公职律师事务所不得发布律师服务广告”吗?我这才意识到,一般人并不了解律师的种类,打广告的某某律所和律师,既不是公职律所也不是公司律师或公职律师,而是面向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普通律所和社会律师。其实,我在回答她的提问时默认了她知道律所和律师的分类知识。
前不久,我到看守所会见一位在押的被告人,他对公诉机关的起诉书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业务进而导致定性错误极为不满,我就跟他一起探讨起诉书发生错误的原因,最后达成共识:一定是检察官对被告人经营的业务涉及的专业知识缺乏了解,因而没有搞清楚相关术语概念,导致定性错误。于是,我们商定:一定要用“无知者”一听就懂、一看就明白的语言,把相关专业问题给法官说清楚。这位被告人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他是懂“知识的诅咒”这种认知偏差及其解决办法的。
为什么会发生“知识的诅咒”这种认知偏差?可能的原因有:信息不对称:拥有知识的人难以理解他人缺乏该知识的状态。假设性偏差:人们倾向于假设他人具备相同背景知识。沟通障碍:不善于用浅显的语言表达深奥的概念,导致对方没法理解甚至产生误解。
既然如此,那么换位思考和同理共情就很重要,要理解他人的无知,主动简化语言,深入浅出地解释专业问题,并注意对方的反馈,及时修正自己的表达,用具体的案例降低理解的门槛。对于律师而言,能当面与客户沟通的,最好不要通过电话或微信交流;能口头发表辩护或代理意见的,最好不要用书面方式。因为发表意见的目的是让人理解并接受你的意见,而由于知识的诅咒存在,电话和书面难以共情,难以反馈和修正。
证明“知识的诅咒”存在的实验是 1990年斯坦福大学博士候选人伊丽莎白·牛顿进行的实验:
任务:她将参与者分成两组——“敲击者”和“听众”。
过程:敲击者被要求在一张桌子上敲出一首著名歌曲(如《生日快乐》)的节奏,而听众的任务是猜出这首歌的名字。
预测:在听众猜之前,敲击者被要求预测听众能猜对的概率。敲击者预测的概率是 50%。
结果:实际的实验结果令人惊讶:只有2.5% 的人猜对了。为什么?敲击者在敲击时,脑子里能浮现着那首歌的旋律、歌词和节奏。他以为自己敲出的节奏是清晰明了的。然而,听众听不到敲击者脑海里浮现的那些信息,他们听到的只是一串断断续续、难以理解的敲击声“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个实验完美地展示了“知识的诅咒”:敲击者无法摆脱自己头脑中既有的知识,从而严重高估了听众理解他们敲击内容的能力。
前面讲了打破“知识的诅咒”的一个方法即理解对方的无知,以深入浅出的方式降低认知的门槛。其实,从沟通的角度看,影响认知判断或沟通效果的还有另外一个认知偏差即“框架效应”,框架效应既会影响人的正确判断,也能被用来提升沟通效率。
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 ,是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概念。从它对认知的不良影响看,框架效应意味着人类的认知和决策存在非理性的一面;同时,既然人们普遍存在走捷径的思维偏好,那么就可以利用框架效应这种认知偏差来“投其所好”以节约沟通的成本、提升沟通的效率。
框架效应是指把同一个事实或观念放置于不同的框架内会使人形成不同的认知,对同一个观点采用不同的表述方式会使人们做出截然不同的决策。即使是知识渊博的人,也跟普通人一样偏向于重视“说什么”而不是“怎么说”,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有时候“怎么说”比“说什么”更重要。也就是说,认知和决策不仅取决于事实和逻辑,还深受呈现方式的影响。
框架效应的典型案例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设计的“亚洲疾病问题”实验。
实验场景: 假设一种罕见的亚洲疾病正在爆发,预计将导致600人死亡。现在有两套方案来对抗疾病,科学估计如下:
第一组被试(正面框架——“拯救生命”框架)。方案A: 200人将被拯救。方案B: 有1/3的概率600人全部被拯救,有2/3的概率无人获救。结果: 绝大多数人(72%)选择了方案A(确定性地拯救200人)。
第二组被试(负面框架——“死亡人数”框架)。方案C: 400人将死去。方案D: 有1/3的概率无人死亡,有2/3的概率600人全部死亡。结果: 绝大多数人(78%)选择了方案D(赌一把,可能无人死亡)。
其实,在600人可能死亡的公共卫生事件中,方案A和方案C在数学上完全等价:拯救200人 = 死亡400人。方案B和 方案D在数学上也完全等价。唯一的区别就是表述框架不同:一组强调“获得”(拯救),一组强调“损失”(死亡)。人们因为框架的不同而做出了相反的选择:在“获得”框架下(拯救生命),人们是风险规避的,他们更倾向于确定性的收益(稳稳救下200人),而不愿去赌一个更大但不确定的收益。在“损失”框架下(死亡人数),人们是风险偏好的。他们宁愿冒险一搏(赌无人死亡),也不愿接受一个确定性的损失(400人必死)。
该实验证明了人并非总是理性的,决策既受风险趋避心理(也是一种认知偏差)的影响,也受到问题表述方式即框架效应的操控。
框架效应的根源与人类的认知心理有关:
损失厌恶:人们对“损失”的感受强度远大于对同等“获得”的感受。失去100元的痛苦要大于得到100元的快乐。因此,当问题被框定为“避免损失”时,会激发出更强烈的情绪反应。
启发式与认知捷径:大脑为了节省精力,不总是进行深入的理性分析,而是依赖直觉和情感做出快速判断。不同的表述方式会激活不同的心理捷径。
参照点依赖:人们对信息的解读依赖于一个参照点。“拯救生命”的参照点是“0人获救”,所以任何拯救都是收益;“死亡人数”的参照点是“无人死亡”,所以任何死亡都是损失。
既然如此,框架效应就被广泛运用于市场营销、政治、法律、医学等领域的人际沟通。比如,在商业营销中,肉类食物标签内容的选择,写“含75%瘦肉”(而不是写“含25%肥肉”)对于生活富裕且减肥成为时尚的城市居民更有吸引力(尽管两种写法并无实质区别)。酸奶标签“98%无脂” vs.“含2%脂肪”,前者听起来健康得多。医生向病人解释手术成功率有90%的成功率与说“这个手术有10%的失败率”,虽然实质上完全相同,但前者会让病人更容易接受手术。在立法领域,为了加税,通常会宣传“对富人征收更多的税来资助公共服务”,而不会说“从辛勤工作的公民那里拿走更多的钱给政府”,因为多数人会选择对富人加税而不愿意对辛勤工作的人加税,事实上老板比打工仔更辛勤。在司法领域,无论作为控方的检察官或代理律师,还是作为辩方的被告人或辩护律师,要知道自己的意见可能因表述方式而影响法官的判断。当案件存在争议而意见又不被采纳时,要主动尝试用新的框架和不同的方式重新表述意见。当然,对于负有客观公正义务的检察官和中立公正义务的法官而言,要防止框架效应带来的认知偏差,避免一般人诉诸直觉情绪和思维捷径导致的错误,应该专注于符合三性的证据证明的客观事实,搞明白在600人面临风险的亚洲疾病案例中“200人获救”“400人死亡”与“400人死亡”“200人获救”在事实上并无差别。要给自己充分的时间进行理性的慢思考,而不是依赖瞬间的直觉反应走捷径。
理解框架效应,不仅能帮助我们做出更明智的决策,也能让我们更有效地打破“知识的诅咒”,更有效地与他人沟通,并看透商业营销、政治宣传和诉讼技巧中的话语策略。
相关推荐




